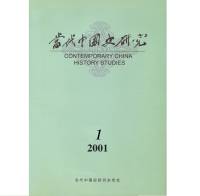【姚百慧】从公使到大使:中瑞外交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 作 者
- 发表/出版时间
- 学科分类
- 成果类型
- 发表/出版情况
- 2016 第五期
- PDF全文
新中国和瑞士的关系在两国外交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从1950年两国建交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除发展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外,还担负着中国同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乃至拉丁美洲等国家的联系工作,成为中国在欧洲开展外交工作的“桥头堡”。[1]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则与瑞士的中立外交传统、摆脱外交孤立、拓展经贸市场等有密切联系。因此,中瑞关系才成为周恩来总理所形容的那样,是“和平共处的一个范例”。[2]
对于中瑞关系,国际学术界已有几本著作专门予以讨论。80在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外交史、瑞士史的著作中,也有零散涉及。81但这些研究有两点不足:一是在史料上,基本未利用中国方面的档案,因此在解释中方的外交决策时有明显缺憾;二是在内容上,在讨论中瑞建立外交关系时,往往只涉及公使级关系,而忽略了互换大使的内容。有鉴于此,本文拟以中国外交部档案和瑞士联邦档案为基础,探讨新中国和瑞士是如何确立外交关系的,侧重于讨论双边外交机构的形成过程。
一、走向承认:中国的变革与瑞士的决定
早在17世纪,中国和瑞士两国就有民间接触。1913年10月,瑞士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随后相继在上海、广州、香港、天津等地设立领事馆或名誉领事馆。1945年,瑞士在南京建立公使馆。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瑞士同国民党的关系面临困境。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新的外交方针,其中之一就是“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3]因此,瑞士若想保护好其在华利益,必须要承认新政权,这在瑞士国内外都面临一定的压力。从国内来说,瑞士公众相当保守,还有部分人激烈反共。[4]但这不是瑞士决策者担心的主要问题,因为公众对中国的情况所知甚少,他们影响决策的能力不大。[5]瑞士更担心的是国际因素,特别是美国的反对。1949年5月,美国国务院指示其驻外使领馆:“美国不主动承认共产党政府,也不对中共寻求承认的活动表示欢迎;西方在承认问题上应建立联合阵线”。[6]6月29日,美国驻瑞士公使、著名的中国通范宣德把美国国务院上述两点通报瑞士当局,并补充说:如果小国要承认,出于某种政治理由,要等到其他大国承认之后才能进行。[7]在这样的压力下,瑞士承认新中国的进程步履维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8]当天,周恩来以外交部部长的名义发出公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通知各国政府。[9]4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把该公函送达瑞士驻华代办热基耶82。接到公函后,热基耶随即转呈瑞士联邦当局。[7] 7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决定,一旦有二三十个国家承认新中国,瑞士亦将予以承认。瑞士不愿是最早的,也不愿成为最晚的。瑞士联邦委员会授权负责外交事务的政治部研究关于承认的具体建议。[7]根据这一指示,政治部起草了两种承认方案:一是“机会主义式”方案,即在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后、其他西方国家承认前予以承认;二是“并入式”方案,即把瑞士的承认包含在一系列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当中,瑞士只是作为“滚雪球”似的承认中的一员。政治部建议采取第二种方案,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让瑞士显得过于突出。[10]因此,瑞士所要确定的是一个合适的承认时机,这里尤其要看英国在承认中国问题上的态度和行动。[11]
1949年12月15日,英国决定承认中国,并把这一决定告知瑞士。英国最初定的承认日期为1950年1月2日。这个消息让瑞士有些兴奋,因为它觉得英国的决定会影响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荷兰、比利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法国等也会很快跟进,“滚雪球”似的承认局面似乎就要发生。[7]瑞士告诉英国,瑞士决定在英国宣布承认后一周或十天左右也在法律上承认中国,在一系列“滚雪球”似的承认之后,瑞士的承认将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12]1950年1月初,瑞士在给其驻华盛顿、巴黎、伦敦的公使馆发送的第1号电报中表示,在英国承认几天后,只要再有几个国家承认新中国,瑞士即将予以承认。[7]
1950年1月6日,英国承认新中国,但瑞士期待的“滚雪球”效应并未发生。除英联邦国家外,只有挪威和丹麦分别在1月7日和9日承认新中国。于是,瑞士改变了计划。9日,瑞士与英国沟通,表示虽然瑞士仍打算尽早承认,但由于其在华利益相对有限,所以不想过于突出自己。瑞士打算等一两周或者更长一点时间看看局势的发展,尤其是想观望其他欧洲国家如荷兰和瑞典的行动,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国内情况和美国对之的关注程度与瑞士类似。[13]1月10日和13日,瑞士联邦委员会曾两次召开会议,与会委员分歧严重,未就承认问题达成一致。之后,芬兰和瑞典分别在1月13日和14日承认了新中国。尽管联邦委员仍有争议,但1月17日召开的联邦会议还是授权瑞士联邦主席兼政治部部长马克斯 · 彼蒂彼爱在法律上承认中国。[14] 就这样,瑞士终于做出了承认的决定。
二、公使级关系的建立:中瑞谈判时间的“短”与“长”
1950年1月17日,马克斯 · 彼蒂彼爱以瑞士联邦主席名义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瑞士“决定在法律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准备与贵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5]当天,瑞士告知国民党驻瑞士“公使”吴南如,称瑞士已决定承认新中国,因此正式断绝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20日,国民党在瑞士的“公使馆”关闭。[16]但新中国对瑞士1月17日的电报迟迟未作回复。这让艰难做出承认决定的瑞士当局既着急又气恼。2月6日,瑞士决定再次尝试。这次是马克斯 · 彼蒂彼爱以政治部主席的名义通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瑞士已任命其驻香港领事司文 · 司丁纳83为驻华临时代办前往北京,与中国外交部联系,询问中方是否同意此项任命。[17]这种缓和的语气甚至在瑞士政治部内引发争议,认为它有辱瑞士的尊严。[14](p.133)这封电报表明瑞士的焦急态度。如果再无回音,瑞士认为整个事情已经完结。[18]
中国终于有了回应。中国认为可接受与瑞士建交的提议。由于马克斯 · 彼蒂彼爱分别以两个名义来电,外交部在回复电文中也起草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回复,第二个方案是以周恩来外交部部长的名义回复。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苏联访问,瑞士政府要求建交的两封电报和外交部拟复电均发到苏联。中方最终决定在第二方案的基础上予以回复。2月1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复电马克斯 · 彼蒂彼爱,承认已收到瑞士的两封来函,表示在瑞士“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之后”,新中国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瑞士建立外交关系,并接受司文 · 司丁纳为谈判代表。[19]
瑞士对中方的回复并不满意。首先,中方提出了瑞士与国民党“断交”这个前提条
件;其次,中方只接受司文·司丁纳为谈判代表,而不是瑞士希望的代办身份;最后,这封信还是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名义回复的,这比马克斯 · 彼蒂彼爱两份函电的身份都低。[14](p.134)不过,瑞士仍决定派司文 · 司丁纳前往中国。瑞士政治部评估了中方可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并提前做了预案。政治部还指示司文 · 司丁纳,谈判要基于互惠的原则,要为使馆人员获得豁免权,保持瑞士在上海、天津、广州的领馆。此时瑞士仍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它希望看看中英谈判的进展。政治部在给司文 · 司丁纳的指示中特别说明,要他随时告知中英谈判的情况。[7]所以,司文 · 司丁纳5月7日才离开香港赶赴北京。
5月16日下午,司文 · 司丁纳一行抵达北京,中国外交部交际处科长韩叙前往迎
接。[20]随后,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同司文 · 司丁纳进行了四次谈判,最终达成了建交协议。
5月26日,中瑞第一次谈判开始。章汉夫宣读了谈判中文稿,提出了中方认为需要先行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瑞士政府对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关系的问题”;二是瑞士政府“对于现在瑞士之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之各种机构及中国的一切国家资财所持之态度如何”。司文 · 司丁纳初步答复说,1950年1月,“瑞士政府一面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即通知国民党驻伯尔尼公使与之断绝关系”。“瑞士政府已将前国民党驻伯尔尼使馆及其中财产档案封存,准备移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依渠所知,中国在瑞士并无其他国家财产”。最后,司文 · 司丁纳表示即将中方所提问题向瑞士政府请示,并于数日内答复。[21]
司文 · 司丁纳将首次谈判结果向国内做了汇报,并得到新的谈判指示。[7]在6月9日的第二次谈判中,司文 · 司丁纳代表瑞士政府正式答复中方,瑞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自1950年1月17日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日起,“即与以前之所谓国民政府残余的所有各项关系,在法律上与事实上均经断绝”,“所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之各种机构,均因此而丧失其正式地位与承认”;“一般而论,所有现在瑞士之中国的一切国家资财,依照瑞士联邦政府意见,唯一之中国政府为瑞士所承认者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具有合法之资财所有权”。司文 · 司丁纳表示:“中国在瑞士之唯一国家资财,为前国民党政府驻伯尔尼公使馆中之家具档案等”。该项中国国家财产“现由瑞士联邦政府政治部负责保管,准备将来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委派之代表”。司文 · 司丁纳主动向中国提交了移交记录。不过,关于中国在瑞士的财产,司文 · 司丁纳又称:“有时因某件之所有权问题,须经法律讨论者,则按一般法律原则办理。因解决争执问题,其权属于司法”。司文 · 司丁纳对此解释说,此系“按照瑞士法律而作之保留,且系纯理论性的”,据他所知,“此刻并无任何中国国家资财在瑞士引起了任何法律问题”。 [21](pp. 396~398)
对于瑞士在第二次谈判中的答复,中国基本满意,不满之处在于两点:一是对在瑞士的中国财产问题,瑞方提出了保留法律解决的途径。不过,中国根据可获得的资料判断,在瑞士的中国国家资产除使馆内之档案文件及家具外,并无其他官方财产。二是在某些国际组织问题上,瑞士立场消极。5月30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次大会上,当讨论到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两国代表建议的驱逐国民党代表议案时,瑞士代表曾投弃权票。6月12日在美国纽约成功湖举行的联合国技术援助会议讨论邀请新中国政府参加时,瑞士代表又投了弃权票。外交部有人曾考虑,在建交谈判时,可以口头提出这是瑞士政府的不友好表现,要求瑞士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承担义务。但周恩来在章汉夫的建议下,未采纳这一意见。[22]因为瑞士本身并非联合国会员国,对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影响有限。而且,在5月15日万国邮政联盟执行与联络委员会会议上,瑞士曾建议新中国代表参加。[23]
6月30日,双方开始第三次谈判。中国对瑞士6月9日的声明表示满意,并感谢瑞士提供的财产移交记录。双方遂进入商谈互换使节的阶段。由于瑞士当时派驻驻外使节,向例均为公使,司文 · 司丁纳在6月30日谈判中曾提醒中方这一点,并询问中国向瑞士是派遣大使还是公使。双方均表示将这次谈判情况汇报各自政府,再行决定。[21](pp.400~401)
谈判成功在即,瑞士却再次陷入犹豫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远东局势因朝鲜战争爆发而遽然紧张起来,以美国为首组建的“联合国军”的军事介入让中美关系更加恶化。面对这种情况,瑞士当局想等远东局势明朗后再做决定,以免让其他西方国家觉得瑞士过于积极。政治部指示司文 · 司丁纳,以政治部已休假为由,表示在9月份之前无法给出具体指示,但司文 · 司丁纳在原则上可以确认互惠的原则。[7]对于这一指示,司文 · 司丁纳认为,远东局势紧张更应迅速与中国建交,否则无法保护瑞士在华利益。此时瑞士延缓谈判只能让人认为瑞士的政策因朝鲜局势已发生变化,让中国怀疑瑞士与美国站在一边,从而削弱瑞士中立立场的可信度。司文 · 司丁纳建议,可先维持代办级水平,暂时避开互换公使。[24]政治部行政事务司司长策恩德同意司文 · 司丁纳的看法,认为要在8月初开始新的谈判。他建议,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向中国派出公使。[7]
司文 · 司丁纳和策恩德的建议为瑞士政治部所接受。8月8日,双方第四次谈判开始,司文 · 司丁纳先表示,因瑞士联邦主席兼政治部部长忙于开会,而他本人又生病了,所以拖延了一段时间。瑞士已决定向中国派驻公使,但因人选尚需经过议会的手续,需要在9月下旬才能提出。在瑞士派驻公使前,希望中国能承认司文 · 司丁纳为驻华代办或临时代办,如果需要的话也可先互换代办。章汉夫回答说:“关于瑞士联邦政府在公使未任命以前派代办或临时代办一节,请瑞士联邦政府自行决定”;关于互换公使问题,将报告政府,有了决定后当即通知。[21](pp. 402~403)从司文 · 司丁纳的发言来看,所谓“迂回的”方式,即先暂时派出代办,稍后再任命并派遣公使。瑞士的建议获中方认可,中方任命冯铉为首任驻瑞士公使,并承认了司文 · 司丁纳驻华临时代办的身份。9月15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瑞建交的情况。[25]这样,中瑞建交成了外交史上奇特的“不对等”案例,在宣布建交时,一方派驻的是公使,而另一方只是派驻了临时代办。直到10月2日,瑞士才告知中方,瑞士任命科莱曼蒂 · 任佐立为驻华公使。[21](pp.415~416) 12月,双方公使抵达对方首都并递交国书,中瑞建交最终完成。
中瑞建交谈判从时间上来看,存在着“短”与“长”的矛盾。“短”是指每次谈判的时间,四次正式谈判均持续20分钟,总计也就一个多小时。这说明,中瑞在具体问题上并无重大的利益分歧。“长”是指从承认到最终建交,两国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即使从第一次正式谈判开始算,也超过半年多。这种“长”固然有中方的原因,但更多的则是瑞士方面的原因。
三、使馆升格:中瑞关系的发展
中瑞建交后,双方的外交关系最初维持在公使级,这与瑞士同其他国家的建交情况类似:瑞士驻建交国的都是公使馆,在外国没有大使馆。而部分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土耳其、梵蒂冈、埃及、巴基斯坦、印度、日本12国,在与瑞士建交时派驻了大使,设置了大使馆。[26]中瑞建交谈判时,瑞士曾指出这种情况,表示中方既可向瑞士派遣大使,也可派遣公使。
不过,向建交国派驻大使和设置大使馆,已成为国际惯例。不少国家也向瑞士表示,希望能派遣大使代替全权公使。有鉴于此,瑞士政府开始考虑使节和使馆的升格问题。1955年2月24日,瑞士向各国驻瑞士使馆递交普通照会,告知当晚将发表关于使馆升格的公告,并附公告全文。当晚瑞士政府发表的公告称,出于国际礼节和惯例,瑞士愿意考虑各国升级驻瑞士使馆的要求,但是否能将瑞士驻外公使馆改成大使馆,将由联邦议会决定,所以,现阶段瑞士政府还不能适用对等的原则,但一旦联邦议会有所决定,瑞士政府也许要适用这一原则。[26]该公告实际上告知,瑞士愿意其他国家驻瑞士使馆升格,但瑞士未必能实行对等,升格其驻相关国家之使馆级别。
上述公告发出后,瑞士政治部交际处处长曾两次向中国驻瑞士公使馆表示:中国是大国,应当设立大使馆。中国认为,自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既然瑞士提出这种愿望,可以同意将中国驻瑞士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26]1955年12月17日,驻瑞士使馆代办彭华奉外交部之命访问马克斯 · 彼蒂彼爱。彭华表示,为促进中国同瑞士间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决定将驻瑞士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征求瑞士政府的同意,也欢迎瑞士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马克斯 · 彼蒂彼爱对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甚为感谢。至于瑞士驻华使馆升格事,他说,瑞士联邦委员会已就某些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事向议会致咨文,估计1956年3月间议会可做出决定,这个问题大致将在6月间解决。最后他说:升格的结果将增强瑞士和中国间业已存在的良好关系;瑞方一俟有原则决定即告中方。[26] 1956年1月3日,双方发表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士联邦政府为了增强两国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已达成协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27]5月,中方任命当时驻瑞士公使冯铉为驻瑞士大使。7月13日,冯铉向瑞士联邦主席费德曼递交了国书。[28]
1955年12月8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发表致议会咨文,要求议会授权将瑞士驻外公使馆升为大使馆,至于瑞士在哪些国家设立大使馆则由联邦委员会之后决定。该咨文称,在这一问题上联邦委员会更多的是从国际因素上考虑,如果从国内考虑也可以不设大使馆,因为在瑞士内部大使不成为一级,与公使没有区别,瑞士使节只有出任大使馆馆长时才有大使职位,离开大使馆后仍为公使。1956年3月,瑞士议会讨论这份咨文,9日,以127票对3票通过了将瑞士驻外公使馆改为大使馆的提议。[26]
瑞士议会的决定扫清了瑞士驻外使馆升格的障碍。中国关心的是瑞士是否会把驻中国公使馆列入首批升格范围。对此,瑞士的回复是模糊的,有时甚至是否定的。1955年12月27日,马克斯 · 彼蒂彼爱在回答苏联公使提出的瑞士准备升格的一些使馆中是否包括驻苏联使馆的问题时给予了肯定回复,但对中国同样的问题却避而不答。1956年5月1日,彭华向瑞士政治部政务司副司长再次询问这一问题,后者答道:瑞士第一批将先设立五六个驻外大使馆,其中有美、苏、英、法、意等国,至于中国,可一步步来(意即第一批不包括中国)。他还表示,有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在瑞士有大使馆,但瑞士在对方国家不一定设大使馆。[26]
中方认为,瑞士设第一批驻外大使馆不包括中国是对中国不够尊重的表现。瑞士这样做,除了所谓“与西方团结”的政治原因外,可能还与中国大使馆设立后迟迟未任命大使有关,因为最近二三个月来,瑞士一直询问大使任命问题。中国驻瑞士使馆建议,一方面可迅速任命大使,另一方面可向瑞士方面正式提出要求,希望其设第一批驻外大使馆中包括中国。不过,外交部认为,鉴于冯铉大使任命事已解决,提出上述要求显得比较生硬。84可以在告知瑞士此消息的同时,表示中方获悉瑞士政府准备将若干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中国政府希望瑞士驻华公使馆能早日升格。[26]
1956年5月4日,彭华拜访瑞士政治部秘书长陈特尔。在彭华遵照中国外交部指示发言后,陈特尔称:瑞士派遣大使的原则(互惠还是根据瑞士利益)尚未确定,但无论如何一定有驻华大使。瑞士向外派遣大使的根据是经济关系、金融投资、侨民多少及政治上的重要性,中瑞贸易额也许并不太多,侨民也几乎没有,但中国是亚洲的政治中心,第一批大使(预计9月间任命)估计会有驻中国大使。9月15日,驻瑞士使馆报告说,据瑞士官方透露,瑞士驻外使馆升格事已内定,第一批在苏、中、美、英、法、意六国设立大使馆。[26]
1957年3月27日,马克斯 · 彼蒂彼爱约见冯铉,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称瑞士拟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公使贝努义85升格为大使,征求中国的意见。瑞士的提议及大使提名迅速获得中方同意,双方在4月12日发表公报。[29] 4月22日,贝努义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国书。[30]
四、结?束?语
瑞士是西方国家中继瑞典、丹麦后第三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考虑到此时美、英、法等大国均未与中国建交,瑞士独立于大国的这一步骤值得仔细分析。瑞士之所以能抵制内外压力做出承认中国并与中国建交的决定,首先,这是瑞士对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综合考虑的结果。经济上的因素是瑞士承认中国的最重要原因,同中国建交有利于保障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的瑞士人的利益,加强瑞士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从政治上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同纳粹国家关系暧昧,战后一度在国际政治中受大国冷落。同中国建交有助于打破瑞士的孤立状态,提高瑞士的国际声望,进而成为东西方的协调者。从文化上而言,承认中国也有助于保护瑞士在华传教事业。[31]其次,这也是瑞士对中国局势客观评估的结果。在最初决策时,马克斯 · 彼蒂彼爱就认为,按照国际法,一个政府当它有牢固的政治结构并且对其领土行使实际而持久的控制,就应当被承认。作为中立国家,不应以别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来决定瑞士的政策。[32]他也曾对捷克斯洛伐克驻瑞士公使称,瑞士承认中国已引起别人不满,但瑞士是现实主义者,不管爱与恨均须承认中国;中国肃清了贪污,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好政府,提高了人民生活,已成了一个强大国家,这是事实。[33]而且,中国将会是未来的强国之一,会对东亚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形势紧张之际,与中国建交才有可能让瑞士在冲突双方之间发挥调节作用。[34]最后,瑞士长期以来奉行的中立主义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中立主义引申的“普建邦交”原则成为瑞士抵制外在压力推进承认与建交的动力之一。[5](pp. 63~65)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遏制政策,拓展邦交的活动并不顺利。到1950年上半年,同中国建交的只有11个社会主义国家、3个亚洲国家(印度、印尼和缅甸)以及2个北欧国家(丹麦、瑞典)。瑞士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在1950年1月就声明承认新中国,对中国而言无疑是非常友好的外交举动。[32](p. 241)因此,中国政府也不失时机地与瑞士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中瑞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首先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体现在双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不断拓展与加强。以贸易为例,1949年双边贸易额仅为156万美元,1950年为617.1万美元,1952年突破1000万美元,1953年突破3000万美元,此后1956年、1957年都维持在3600万美元以上。[35]
中瑞建交拓宽了双方的外交舞台。就中国而言,在中法建交前,中国驻伯尔尼的外交使团成为中国在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中国驻瑞士使馆成为沟通中国与欧洲甚至是美洲、非洲未建交国家的重要桥梁,这些国家的政界、商界、记者等人士多先和中国驻瑞士使馆取得联系后再前往中国;而中国相关人士也通过瑞士中转前往未建交国家。此外,利用瑞士中立国的地位和众多国际组织所在地的地理优势,中国也在瑞士开展了多层次官方和民间的交流活动。驻瑞士使馆成为中国开展对外活动的重要基地。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建立外交关系,也提高了瑞士的国际地位,让瑞士进一步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外交上的孤立地位,在解决与中国密切相关的远东问题时瑞士有了一席之地。1953年,瑞士成为朝鲜半岛“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成员。曾任瑞士驻华大使的周铎勉坦言:“这表明瑞士中立国的价值和她致力于国际和平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如果瑞士没有在这以前与北京政府建立起信任关系,就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国际承认。”86
[ 参 引 文 献 ]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174页。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
Ariane Knüsel, Framing China : Media Images and Political Debates in Britain, the USA and Switzerland, 1900~1950, pp. 239~240.
Nicole F. Stube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Switzerland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Swiss Side of the Story, pp.34~38;Michele Coduri, La Suisse Face à la Chine: Une Continuité Impossible? 1946~1955, p.10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9,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p.17.
Berne, Archives fédérales, E2001(E), 1967/113, Vol. 154.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Notice pour le Chef du Département–Reconnaissance du gouvernement communiste chinois”, 27 Octobre 1949, in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Suisses, 8207.
Regula St?mpfli, “Die Schweiz und China, 1945~1950”, Studien une Quellen, Band 13/14(1988), S. 104.
“Telegram from Berne to Foreign Office”, No. 317, 19 December 1949, FO 371/75827, 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
“Telegram from Berne to Foreign Office”, No. 8, 9 January 1950, FO 371/83280,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
Michele Coduri, La Suisse Face à la Chine: Une Continuité Impossible? 1946~1955, pp.118~119.
“Télégramme du Président de la Confédération suisse Max Petitpierre à Mao Zedong”, 17 janvier 1950, in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Suisses,8016;廉正保、王景堂、黄韬鹏主编:《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1955)》,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390~391页。
Berne, Archives fédérales, E2001(E), 1967/113, Vol. 160;Regula St?mpfli, “Die Schweiz und China, 1945~1950”, Studien une Quellen, Band 13/14(1988), S. 104,p.75.
Berne, Archives fédérales, E2001(E), 1967/113, Vol. 154;廉正保、王景堂、黄韬鹏主编:《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1955)》,第391页。
“Letter from British Legation in Berne to Scarlett”, 10 February 1950, FO 371/83285,in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0页;《我方致瑞士政治部主席彼蒂彼爱的复信(1950年1月21日~ 2月10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0011-03。
《瑞士派遣代表来京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人民日报》1950年5月17日。Michele Coduri, La Suisse Face à la Chine: Une Continuité Impossible? 1946~1955, p.139.
廉正保、王景堂、黄韬鹏主编:《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1955)》,第393~395页。
《章汉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我就谈判过程中提交的有关问题的答复(1950年6月17~30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0011-07。
“Télégramme de Stiner(Peking) au DPF”, No. 15, 24 Juillet 1950, in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Suisses,8272.
《我与瑞士建立外交关系 冯铉受任为我驻瑞士公使 瑞士派施禔纳为临时代办》,《人民日报》1950年9月15日。
《中国、瑞士两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及任命使节事(1953年2月24日~ 1957年4月30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0332-01。
《我国驻瑞士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人民日报》1956年1月4日。
宋恩繁、黎家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
《瑞士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人民日报》1957年4月13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439页。
他石:《瑞士联邦700年(1291~1991)》,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223页。Ariane Knüsel, Framing China : Media Images and Political Debates in Britain, the USA and Switzerland, 1900~1950, p.248.
他石:《瑞士联邦700年(1291~1991)》,第240页。
《瑞士主席谈瑞士承认中国后的反应(1950年12月26日~ 1952年12月26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0192-01。
Regula St?mpfli, “Die Schweiz und China, 1945~1950”, Studien une Quellen, Band 13/14(1988), S. 104,p.76; Nicole F. Stube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Switzerland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Swiss Side of the Story, pp. 60~63.
李清泉:《瑞士七年》,《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 对外贸易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494页。